德国开始扩军,历史的重演?
作者:小二胖
来源微信公众号:智库百晓生
德国是一个很神奇的国家,发动两次世界大战,又均以失败告终。
然后还能缓过劲来,重新成为世界强国之一。
1. 历史回眸
1945年,随着纳粹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彻底失败。
德国不仅丧失了主权,其国防军也被战胜国——苏联、美国、英国和法国——强制解散。
这些战胜国历经一战和二战,担心德国死灰复燃。
因此,战胜国推动了“非军事化”政策,旨在从根本上杜绝德国再次成为战争策源地的可能。
德国由此步入了一段被占领、被改造、被去武装化的历史阶段。
然而,冷战的铁幕很快落下,地缘政治的现实迫使西方盟国重新审视德国的战略价值。
1955年,《巴黎协定》生效,西德获得主权国家地位并加入北约,这为德国联邦国防军的建立铺平了道路。
德国战败十年后,1955年11月12日,联邦国防军正式成立,首任国防部长西奥多·布兰克向首批101名志愿兵颁发了委任状。

这一仪式,标志着德国在战后十年,重新以“武装力量”的身份登上了历史舞台。
虽然德国内部对重新武装存在分歧,但是,正如军事历史学家松克·奈策尔所指出的“
德国人从来都不是和平主义者
最终,主流民意支持了康拉德·阿登纳总理的防务政策。
1956年1月20日,时任国防部长布兰克、总理阿登纳到莱茵河畔安德纳赫视察首批联邦国防军志愿兵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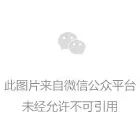
1957年,阿登纳领导的联盟党以绝对多数赢得大选,也印证了重新武装在国内政治中的合法性得以确立。
整个冷战时期,联邦国防军深度融入北约防御体系,其使命被严格限定为“保卫德意志联邦共和国”。
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,其兵力一度达到49.5万人的峰值,成为北约对抗华约集团的中坚力量之一。
1989年柏林墙倒塌,1990年两德统一,世界格局剧变。
随着东方威胁的消失,德国所处的安全环境发生了根本性转变:周边皆为友邦,大规模地面入侵的威胁似乎已成历史。
联邦国防军随之进入了长达三十年的“战略收缩期”。
东德人民军被解散,其约9万名官兵经过筛选后部分并入联邦国防军。
军队的总规模开始持续缩减,从冷战高峰的近50万人,逐步下降至20万人以下。
国防预算被削减,装备更新放缓,军队的任务重心也从本土防御转向海外维和与危机应对。
2011年,德国更是全面中止了实行长达55年的义务兵役制。
这一决定在当时被视为“和平红利”的体现,是德国自信于其永久安全的象征。
然而,这种长期的和平主义倾向与军事收缩,也埋下了隐患。军队装备老化、人员短缺、战备水平下滑等问题逐渐暴露。
尽管其间德国参与了科索沃、阿富汗等海外行动,但其军队的整体结构与心态,仍更多停留在“和平兵团”的定位上。
3. 转折
2022年2月爆发的俄乌冲突,对欧洲安全秩序构成了自冷战结束以来最严峻的挑战。
卧榻之侧的现实压力,于是,德国总理朔尔茨宣布设立千亿欧元的特别国防基金,并承诺将国防开支提升至GDP的2%以上。
这标志着德国安全政策的根本性调整。
而现任总理梅尔茨领导的政府,则更近一步,明确提出要将德国联邦国防军建设成“欧洲最强大的常规军队”。
这一目标面临的核心瓶颈之一,是兵源。
仅靠自愿入伍,无法满足军队大规模扩充的需求。
因此,重启义务兵役制,从政治议题迅速转变为实施方案。
2025年8月德国内阁通过的新兵役方案,可以视为义务兵役制全面回归的“前奏曲”。
要点如下:
简言之就是,先吹风,再执行。
新兵役方案先以调查和体检的形式让国家权力介入,既是对社会承受力的试探,也为未来的全面强制积累了行政基础。
4. 争议与冲突
兵役制的回归,在德国社会引发了复杂的争议。
一方面,如18岁的青年代表盖特纳所言,许多年轻人愿意在“国家需要时”承担责任,但他们质疑政府推行法案的方式。
另一方面,总理梅尔茨公开表示,2011年中止兵役制“无疑是一个错误”,这代表了政治精英层对过去战略短视的反思,以及对重塑公民与国家国防之间联系的迫切愿望。
争议的焦点,再次回到了那个经典的伦理与法律问题上:
良心拒服兵役权。
因为根据德国《基本法》,公民有权出于良心原因拒绝拿起武器。
新法案延续了这一规定,但设置了严格的门槛:
拒服者必须主动提交书面声明,详尽阐述其基于政治、宗教或道德理念的良心动机,并明确指出“恐惧”不能成为合法理由。
这一规定在实践中将如何界定“良心动机”?
会不会变成,“说你没有,你就没有,有也没有。”的情况
这不仅是法律程序问题,更是国家权力与个人自由的一次重新界定。
德国重启兵役制的决定,绝不能简单视为对俄乌冲突的应激反应,其背后更是多重因素的叠加:
德国的这一转变,是其战后历史上又一个决定性时刻。
它标志着“以商业和规则为导向”的后冷战时代德国,正在向一个“认识到力量政治重要性”的新德国演变。
义务兵役制的回归,不仅是军事人事制度的调整,更是一种国家战略文化的重构。
这一过程必然伴随争议,但其方向已不可逆转。
一个重新武装起来、并愿意承担更多防务责任的德国,究竟是欧洲稳定的“定海神针”,还是会成为地缘博弈中的不确定因素?
历史是场圆舞曲,轮回的只是时间。















